回歸仲景原意 在臨床中詮釋經典
近讀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出版的經方新著《黃仕沛經方亦步亦趨錄——方證相對醫案與經方問對》,獲益匪淺,感慨良多。黃仕沛先生出生于中醫世家,幼承庭訓,正步杏林,從醫多年,體驗非凡。上世紀90年代起轉攻仲景之學,于經方致力尤勤,尤其服膺仲景方證之學,大有“覺今是而昨非”之感。書中不僅通過大量經方治療危急重癥病案展示出一位當代中醫臨床名家療效卓著、屢起沉疴的大師風范,更展示出先生對中醫學的真摯感情,對中醫學子的提攜厚愛。黃師諄諄告誡后學學習中醫學的關鍵與捷徑——方證相對,筆者對此感同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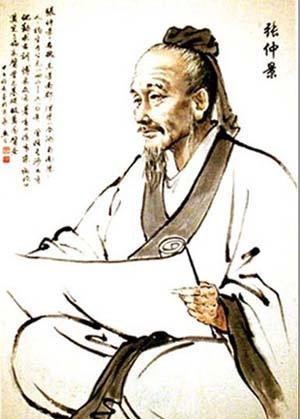
忠實仲景原文,亦步亦趨
黃師常謂“仲景步亦步,仲景趨亦趨,是學習經方最基本要求,也是最高境界”,黃師指出對醫圣亦步亦趨,以仲景書為法,探索經方的辨治體系和用藥規律是學習捷徑所在。而學習、掌握、運用經方的基礎與關鍵則在于忠實仲景經典原文。臨證時,只有熟練掌握方證條文,才可以辨別方證進而據證用方。書中記載的大量經方驗案與經典原文高度相似,可以說是經典條文的高頻再現,是經方醫案的原味翻版。如“胸中一股寒氣上沖咽喉,時而數日一發,時而一日數發,發作時覺胸中窒息感”即“胸痹心中痞,留氣結在胸,胸滿,脅下逆搶心”之枳實薤白桂枝湯證;“上腹部跳動感半年”的十二指腸球部潰瘍即“心中悸而煩者”的小建中湯證;應激性腸炎患者的“大便失禁,清稀如水狀,量多”即“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的理中湯證等。
拓展運用經方,深入挖掘
由于經典原文敘癥極其簡略,這給我們學習繼承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因此如何做到古方新用、古方今用,還原、豐富、充實方證主治就成了學習經方的重要任務。黃師以其深厚的理論功底和扎實的臨床實踐經驗,深入挖掘經典高效古方方證,拓展經方證治,還原經方劑量,讀來啟發甚多。以小續命湯為例,該方原文主治中風痱,黃老將本方拓展運用于治療多發性硬化、脊髓膜瘤術后脊髓萎縮、急性胸頸段神經根炎、帕金森綜合征、胸腺瘤術后放療后脊神經受損等出現四肢肌力下降,肌張力降低,下肢活動不利、乏力,感覺障礙,麻痹不仁,言語不清,吞咽功能障礙,神經性疼痛等。黃師對方證的臨證發揮還有很多,如不僅將木防己湯用于治療關節疼痛,指(趾)端如鼓槌狀,還用于慢性肺源性心臟病肺動脈高壓出現指端發黑、杵狀指的治療,認為這是條文“面色黧黑”的延伸;甘草瀉心湯治療銀屑病、慢性結膜炎、手足口病;防己地黃湯、風引湯治療老年女性的嘴巴不自主抖動,腦梗后肢體不自主舞蹈等。
不尚玄理空談,力倡客觀
“仲景之學,至唐而一變”,自宋以降,中醫學思辨盛行,徐靈胎針對當時醫界詭辯盛行深有感慨,“今則以古圣之法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陽虛、陰虛、肝氣、腎弱等套語概之”。黃師敏銳意識到該問題的嚴重性,臨床不尚玄理,不尚空談,不尚浮夸,反對以虛無飄忽的理論解釋仲景學說。通過文獻考證發現,《傷寒論》與《內經》并非同一傳承體系,若以《內經》理論解釋仲景學說則大失圣人之意,所以黃師反復告誡學生,“須知仲景用藥,皆以證為依據”。如麻黃湯中桂枝為桂枝證而設,不僅能主治惡寒發熱頭痛,更能定悸,減輕麻黃發汗太過而出現“心下悸欲得按”之弊;芍藥甘草湯并非“酸甘化陰”所能解;血府逐瘀湯中桔梗、牛膝一升一降只是基于良好主觀愿望的一廂情愿,桔梗去之也無妨等。
黃師力倡回歸仲景原意,主張在臨床中詮釋經典,反對以虛玄的理論敷衍解釋傷寒,甚至在其《陋質銘》中說“可以丟素問、去難經,無生克之亂耳,無六氣之無形”,看似偏激,但其言論切中時弊、擲地有聲、振聾發聵。況且黃師也不完全反對《內經》,只是強調要把有限的精力放在重點上,而這里的重點則指“方證”。柯韻伯曾說,“夫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門,人人可入,而使之茅塞如此,令學人如夜行歧路,莫之指歸,不深可憫耶?”中醫學大道至簡,而方證則是中醫學的核心所在,是執簡馭繁的關鍵。總的來說,筆者認為該書瑕不掩瑜,不失為學習經方之一大助,為嘉惠杏林的一部應時佳作。
本站所注明來源為"愛愛醫"的文章,版權歸作者與本站共同所有,非經授權不得轉載。
本站所有轉載文章系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確注明來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轉載的媒體或個人可與我們
聯系zlzs@120.net,我們將立即進行刪除處理

